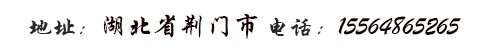陈陈相因小说怪物下部
|
有人去过北京中科医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fr=aladdin 《怪物》 作者:陈陈相因 (高二所作,修订版刊《石油文学》年02期) 《带我到山顶》和《归途》呈现出一种贴近现实的臻于成熟的写作,老练而完满,《忏悔录》和《画岛》却充满奇思异想,也呈现出文本的多种可能性。《怪物》和《木兰舟》也在相似的路径上书写了现实世界之外的某种神秘性。——第六届“青春文学奖”初评作品导师综评朱婧南京师范大学 90后油三代对世界有一个挑战的姿态,心理上是激进的。怀有强烈的看世界的雄心,他们的心灵是开放的。这种观念很显然会点燃他们的生命热情。然而,从空问角度讲,他们是缺少乡愁的,对于他们来说家乡是稳定的职业,而她在小心翼翼保护着梦幻的故事。他们在更为激进的意义上,把石油城风景带给他们的战栗、迷惘转变成独转特的审美特权。写作者陈陈相因充满奇思异想的写作实验,大胆而生动。他们确实引入了新的表达手法,这是他们在文字之中所获得的“最初的激情”仅就写作成熟度来讲,后辈的写作者看起来更胜一筹,但读起来似乎还不满足,或许还不能说他们已经逾越前辈的表达。希望随着他们阅历的加深,止步手对文字的把玩。但是希望他们继续保有对文学想象和激情。——钟好好《再叙事:石油文学的经验》 三号词典:眉寿书 八岁那年,父亲送我了一个笔记本,封面是烫金压花工艺缠绕的藤蔓。他打趣地说:“这是一位有灵性的倾听者,如果你用语言对它撒谎,它会伤心,会失灵,会焚稿。”姐姐用手一碰这本子,藤蔓竟舞了起来,像是一群邀我共舞的女郎。她的手也变成了翠色的藤蔓,扭动着一段琴声。我当即决定把我们的故事写进里面,我的腐朽,她的奇遇。我很小的时候还不会写什么东西,偏偏只要姐姐在身边,我就灵感迸发,就像是那些看见缪斯的写生者。我也常常倾听姐姐说的话,甚至拙劣地偷窃她的语言。姐姐好像有神奇的皮肤,万籁可感。她整个人是敏感的含羞草,可以捕获风声、雨声甚至心声。我就不能,我是个聋子、是个哑巴,无法对着世界作答,更别说什么解释了。悲催的现实让我显得无比臃肿。时而压抑,时而忧伤,时而欢快的跌宕生活让我如此沉溺。我偶尔会偷偷带她出去,并将这种行为称之为“宇航”,我需要把姐姐隔离起来,为此我们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把鱼缸擦亮套在她头上。她架起这微型的温室,肩膀上开始有花朵破土而出,目眩神迷的黄蔷薇,绕着她的脖子长出,像大张旗鼓的火焰。她的脸颊被划破了,小小的伤口里就又长出了红色的小蔷薇。她一打喷嚏,花朵又缩了回去。姐姐能和万物对话。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去动物园或者植物园,和她走在一起,我听着动植物七嘴八舌地讨论着人类、天气、季节,自从他们被培育和圈养,对人类多了些谄媚或厌恶。因为少了竞争,他们的讨论更像我同学之间的窃窃私语。每天被规范了作息和活动的指定范围,他们讨论最多的就是今天何时闭馆,三餐吃什么。他们会一起讨论某个异性的相貌,但婚配还是要听饲养员们的“媒妁之言”。总之,园里和园外都是一样热闹却寂寞。我们循着呼吸找到过一只跑出来的解忧兽,当时它是跟着姐姐从困世山的绵薄林里跑出来的,她的长相白狐狸一般,脖子上长着一绺类似马鬃的毛。她躲在车胎下面,见到姐姐才踱步探出身来。那时候我抱着吱呜的解忧兽,回想时在《眉寿书》上写:“它亮晶晶的身体像毛茸茸的雪山,如果冬天的雪都变得温暖,是否一场大雪就像一场亲吻呢?”我抱着这解忧兽走了一路,它竟在我怀里大哭起来,搞得我的衣服全都被她的眼泪漂白了。她边哭边变得透明,直到消失在我怀里。后来姐姐和我说,那是江泌小时候,它住在困世山的绵薄林里,那里的树全部都是平面的,像画一样,江泌每天都盖着树睡觉。姐姐到了那里,江泌还认出了她这救命恩人,跳到她背上蹭她,决定成为她的宠物。一日,江泌睡在姐姐肩上,睡着,睡着就变成了姐姐的发尾。在困世山,姐姐还救过迷路的受伤幼豹,他有弯月一般的身形,皮肤却不断长出霉斑。他独来独往,神态像娶亲的车架,所到之处,花草腐烂成一滩浓稠的芳液。他喜欢躺在高高的树枝上咀嚼黄昏和黎明,当他在傍晚下张口吃掉它们,他身体上的那些霉点就开始闪烁。鹘突亲近他身体就会变成污水,树在触摸他的皮毛之后会立马变成枯枝。姐姐怀疑瘟疫和他有关,在接到一位鹘突举报后前来调查他。姐姐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秋满。秋满属于自投罗网,他很喜欢姐姐的鸟巢,经常一整天一直躺在因他而死的老树上看着姐姐,尾巴垂下来的时候秋千一样风流。我想到秋满时,常期待姐姐“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的一天,替姐姐在《眉寿书》上写下:“第一次我看见你的时候,我笃定地以为你是飘落的银杏。想给你温一壶血或者熬上一锅肉款待你,却没等你下那树冠,将所有春夏的晨露给我做酒,就让翠羽变成落英。你不知道,放飞一头喜爱的猛兽就如纵容一束光溜走。”姐姐不会把她嘴里的那些诗变作文字,因为她恐惧它们。她觉得它们冷酷无比,像真理的监牢,一个字囚禁着一个事物。当她首次打量文字时,她借着我的口吻说:“那是一道恐怖的列车,带着所有情感的死囚。那些句子,是不能复生的诗。它们是文明权力的毛虫,让你必须学习和倾听它们。你无法和人类割裂,你必须要靠着这些隐藏好自私参与进去。”“没有人能在文明里全身而退,妹妹。”我至今都记得她这句话,因为我学会了那些我和族群连接的语言,反而消解了内心的本义。我在开口时有了太多丢失和差池,并在诉说的过程里得到了终极的孤独。姐姐和秋满约定找到医治方法,让他每日过来问诊。她指挥风在他尾巴系上银铃。姐姐飞上树去,观察他发霉的身体。那些霉斑近看是黑色的漩涡,它们运动着,放上去的花瓣会被卷进去。姐姐试图读出他的心,却听见那些深渊在和她诉说:“你是谁呢?长在秋满的身体里?”“鬼魂,被关押的智慧。”他的声音十分粗犷。“来自哪里呢?”“世界的另一边,创造这个世界的人,把她终极的智慧关在这里面。”“那我该怎么拯救你?”“为我解忧,让我不再因为思考殚精竭虑……”我在《眉寿书》里这样写道。秋满跟着姐姐很久,姐姐看他经常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剪了段发尾给他做了围巾。江泌就这样从睡梦中跑了出来,可爱的江泌每天都会自导自演戏剧给秋满看,她的身体还有多个声部可以分饰多角。秋满看了经常大笑,他身上的漩涡不断浮出,直到最后变成了黑色的实心斑画。但他的身体还是一触碰就会让万物迅速凋残腐烂,江泌看他心疼,索性抻开自己的身体,将自己变作一架神轿,驮着他四处云游。这样他可以一直脚不着地。“你怎么像个神经病似的,好像每天就不见你做别的,一天到晚都在写这本子,怎么也不想和我们分享分享?”我的回忆被凑上来的同学打断。我本一句话不想和她说,无奈又要搬运些无用的语句来搪塞她。“没有,就是写写日记。”见她将信将疑,我又接了一句:“诶,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高考之后的命运?”“没有,为什么要想,这很重要吗?上大学、谈恋爱、读研、结婚、升职加薪、买房买车、生子、抚养孩子……”她说出的那一连串事件,甩出的沉重的铁链将紧紧捆住。我感觉这套刑具离我越来越近。“每一条道路都值得怀疑。”我脱口而出,声音故意放低没让她听个真切。“你说什么?”“没有,我只是,只是觉得自己活得有些疲倦。你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吗?你又是如何确定眼前的一切就是知识?你觉得我们就算结束了现在的考验会获得自由吗?我们能有幸福的命运吗?”我不由自主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以前和姐姐在一起的时候,姐姐总会和我聊这些事,后来我十六岁生日那天,她对我说:“明天我就要逃离这里了,你长大了,我必须回到困世山上,回到你为我构造的世界,你忘了吗?”“哈哈,人不应该发问,人应该接受答案不是吗?何况这不是每个高中生的困扰?”“不,你能理解那种感觉吗?非要逃离现实的感觉,你身体里有一些率先苏醒的、创造性的东西像浩瀚的宇宙在不断扩张。”“不,其实也有答案,就是陈同学你其实是个诗人。”她拿腔拿调地讽刺我。我不知道该怎样接话,兀自点点头宣告了她言论的胜利。讨论结束后,她就悻悻地走了。剩下的休息时间,我摘下近视镜,枕上与我相濡以沫几年的课桌,披上拥抱过夜风的外套,这样的梦是一生所爱。片刻的梦,我能感觉我是姐姐的须臾。苏醒后白炽灯边的飞虫,在我模糊的目光中像极了海上围拥的海鸥,绕着白光似绕着白盈盈的浪,心想把它们裁下来做围裙。恍惚间的事物最可爱。书本城池中,夹在其中的卷子是宣布投降的旗帜,有了逶迤的红笔点缀之后才变得平易近人。笔袋似是寒素的妆奁,盛满我朴实无华的时光。笔能勾勒出我未来的眼眶,却描绘不出漫长的寂静,我要和昏天暗地的时光作别,要和我贪图享乐的时光作别。我很恐惧,我将在文弱的城市流浪抑或在荒芜的地方流放?很少有人与我相伴,很少有人对我坦诚。我害怕在年老的时候会忽然想念,想念永远睡在那里的飞虫。也许,它就是那毫无意义,又是隐隐作痛的。我爱知识,但我更恐惧它。我害怕真理真正的到来,痛恨人们要求孩子们走同样的路径通向它。八岁出事那天,我回到家整个人都是沮丧的,除此之外,还有迷惘。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是我的厄运吗?“那是文明掩盖的角落,那些放纵的,随意而为、欺软怕硬、伺机而动的暴力,那些不需要理由和形式化的行为,才是和我们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道德伦理时常是滞后无稽的。”我恍惚间听到了姐姐的心声。我推开密室的门,与其称其为密室不如说是套间,称其为密室因为它总是有些阴暗。她房间的窗是从天花板上开的,圆窗下面就是泳池。每当有晚霞慢慢经过的时候,汹涌的紫色就从水面上掠过。姐姐经常在水底。她变成一条人形的孔雀鱼,腰身似波浪的一部分,脊背是流动的霓虹,光下每一块皮肤都似鳞。水下,眸子是七彩的转轮,手臂划开蝴蝶翅膀的弧度。她见我进来探出头来,说话时竟吐出了几个缤纷的泡泡。“你……吃了肥皂吗?”我问。几天不见,我不晓得姐姐在泳池里养了两株溪客。这泳池俨然成了姐姐的池塘。溪客白白的花苞上有黄昏婆娑瓣尖的红晕。我没找到她,便走入了林道。步入林道,我隐约看见什么动物在森林里。我走上前去,才发现那是一只米白色的独角兽。她不过乳羊般大小,向我走来,蹄下熠熠生辉,所经过的石头都变成剔透的宝石。我也向她走去,脚下的路变得亮晶晶的。相遇,她竟俯下身子,将前蹄放下,跪在了我的面前。我小心地抚摸着她的皮毛,又按了一下她的角。她的角徐徐收了回去,耳朵两侧又长出两个角,身体由白色变为栗红色,毛上生出有序的白斑。她的那一对角在不断生长,耳朵也随之变长直立,直到她的角上出杈来,长出三四片红梅这才停止。《尘荒纪》里讲的“灵”是真实存在的。我的“灵”就是我姐姐,她是我一生的缪斯。为了保护她的安全,我宁愿一个人面对寡情的地理,心随着死板的经纬精细到每片湖泊、每个岛屿,杜尚别、斋桑泊、七岛港、玛瑙斯……我继续着和那些冷血知识的纠缠周旋,为的就是姐姐的平安。她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很奢侈。她在笼焰山画石屏给我看,还有那些像极雉堞和云霞的石头。那里地表温度极高,所有的石头都是软的,可以任意雕刻或重塑。她跟我说过团酥河的河水是白色的,但是她没办法给我画下来。“我想要一杯团酥河的河水。”我写在《眉寿书》上。我不知道困世山的具体位置,只知道困世山有道门。那山不是所有人都能去的。必须是怪物,像姐姐这样的怪物。姐姐是那么洁白、纤尘不染,就像雾凇挂在树上。她是那样令我歆羡,即使我们,我们有着一模一样的外表。四号词典:家庭审判 “我不想每天坐在家里对着缝纫机、碗筷,还有只有一种颜色、让我联想起沙漠的地板。我想要朋友,但却想要回避人群,人群的毒气太重了,我会病入膏肓的。那些人会用虚伪粗鄙的语言告诉我该怎样过活,却无法告诉我怎么去欣赏、感动和烹饪。所以我想去一个属于我这种怪物的地方。”我翻到《眉寿书》姐姐去困世山的那天自己写下的东西。有时候我很难分清楚这到底是我的心境还是姐姐的心境。姐姐还在的时候经常做衣服给我,但我只在密室里穿,她用来织花纹的线每种都有植物香,红色的是海棠香,紫色的是迷迭香,蓝色的是鸢尾香……棕色的有树枝的清香,白色的是满天星,细针一穿就多了几个零落的白结。姐姐缝的斗篷有时是夏天的味道,有时是春天的味道,裙摆的流苏常常是倾泻的瀑布。充满春天气味的斗篷之中,穿上就有燕子从我胸膛飞出。她在密室里养的溪客生得喜旺,叶子大些的用来做了雨伞,小的用来喝水或者装果子。有天姐姐在荷叶底下发现了一个怎么都融不进水里的水滴,她把它捅破,有一只五彩斑斓的小鱼出生。七岁之前,我还对姐姐没有很多概念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并没有那样亲密无间。姐姐说过清晨不要去找她,那是她蜕皮的时间。我误闯过她的房间,清晨的房间和其他任何时候的房间都不大一样,安静,神秘。姐姐裸身,肩胛骨打开巨大的贝壳,腰窝盛满河流。她在熟睡,头发像是蜿蜒的山路,让我想要安置马车经过,挑拨她的发丝做成风沙。她身下的圆床巢般包裹着她的身体。她安详地侧卧,身上立着几只鸟。那些蓝鸟和白鸟在她的胳膊上调羽,好奇地看着她的脸庞,似乎那里长了红樱桃。我这才看清她是浮在床面上的,那床是灌满了水的圆缸,姐姐的腰部似乎有伸到水底的根。她的血脉晶莹发亮,就像有星光在她身体里。那天我的身体根本不听使唤,竟吻了她的肩膀。她惊醒,回头望我,眼睛是深蓝色的,角膜和虹膜之间盛着来回晃荡的水,她稍有动作那水就会跟着起伏。这曼妙的眼波咒语般吸引我打开她。我鬼使神差地抱着她,嘴唇像小蜘蛛一样游走在她的肩膀和脸庞间。她见我这样,以为我要伤害她,愤怒地咬了我的肩膀。第二天那咬痕开始长出苔藓,苔藓在伤口处连成一片,脱落后才愈合。在那之后我绝口不提此事,但是姐姐好像失忆了似的,因此我对她愈发好奇。现在想来,我那时候就想成为她了。我为了怀念这件事,在她走后养了一盆青苔。无论我怎么照顾、虐待、宠溺,它们都始终如一。它们不能做指南针告诉我姐姐在哪个方向。谁可与玩斯遗芳兮?长向风而舒情。我捋顺了记忆之后,晚自习的铃声正好响起。就是在这个晚上,我临时决定动身去找姐姐。正当我这样决定的时,姐姐正站在困世山最高峰冽凉山上。下过雪后的冽凉山,冰川华美无暇,静庭鹤在姐姐挖的井旁边优雅地鞠躬。静庭鹤是困世山的钟表,一个时辰弯一次身子。困世山最近云迷雾锁,阴云几度不下,人口一度减少,寸草难生,似有灾难即将降临。姐姐不得不翻山越岭飞去更远的冽凉山。她曾画了冽凉山的地图给我。就在我被大雨惊醒的某个夜晚,我看见有层峦叠嶂在我床单上立起,一时间融化的冰水自山峰倾泻流下,变成这群山之间的长河。我想记住那地图,可那地图消失得太快了,像被掳走的,我根本没办法完全记下。这个晚上我失眠了,我一直在思考那些往事。往事是一条宝蓝色的缎子,我纵身一跃就变成了一条永恒的鱼图案,在记忆里漂泊,在未来里惆怅。不会呼吸的鱼、健忘的鱼、因为迷茫而自寻死亡的鱼。我开始麻木地喜欢极了拘束,不太喜欢尝试,也不太乐于助人。很多时候咀嚼自己的生活就像观察溶解的药片。狰狞、教训、苦难、寂寞,还有终归的平凡以及中规中矩的善良,最终都会变成绚烂或腐烂的东西,成为我百毒不侵的原因。我不知道该如何和庸俗的自己和解。或许我应该祝福自己,可我最害怕的是万一自己有天背叛姐姐向世俗投降,我们努力搭建憧憬中的世界,最终却两手空空。青春是战火纷飞的,无暇的东西会自己磕出瑕疵,胚胎会摔碎自己寻找成长。在自己的追求中,我常对世界产生误会,常告诫自己不要和它较真,但是这种无解的感觉,显得它难得,让我流连忘返。我无法预见成年后自己的压抑,也想过为自己破茧成蝶的那些光荣岁月会变成烈酒,汇成河流。我们的那些初衷变成鹰隼,飞翔时分不出高下,也逃不出云霄。我羡慕那些还没有醒来的人们,他们在梦境中酣睡,他们从未尝过怀疑的滋味,因为他们是幸运的人,永远能去到自己的远方和高处。有梦想的人反而踌躇怅惘地过着颠簸一生,永远品尝着万蚁噬心的滋味。我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呼唤着我,也许是失眠产生的幻觉,我觉得此地不是我的应许之地,我想要踩死那条鱼。因此我打算在凌晨出发,我想要去找姐姐。太阳升起的时候,《眉寿书》中的纸竟发出了雪光。“我们将相聚于此,合二为一。”家乡最近连续阴雨,雨水冲刷过的每个角落都显得格外苍凉。深夜,我起身把《眉寿书》装进包里,扎好头发,穿上衣服,悄悄潜出家门,去了车站。凌晨的车站人不多,我一个人站在售票厅的屏幕前搜索着那些目的地。我想冽凉山一定很远很远,至少比困世山远得多,可是现在我站在售票厅里却觉得这几个字才是离我最遥远的。就在我发觉自己的荒唐时,我见到了父亲。“我听见你房间里有动静,才一路跟来的。”他的表情十分严肃,语气却小心翼翼,没有责备的感觉,却夹着一丝惶恐:“你怎么一个人跑来车站,要去哪儿?”我也有些惊慌失措,讲道:“我要去找姐姐。”我说这话本是要试探他的,我怕他责备我。我们之间沟通总是很少,大部分时候我们不清楚对方的底线在哪。他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没说话。为此我忽然有了请求他的念头,想说说心里话给他听,便急切地继续说了下去。“我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真的太想她了。我一个人太孤单了,时常感觉只有姐姐懂我。我想去困世山,想去她的世界,但是我不知道那些地方在哪……”说到最后几句的时候我鼻子酸了,就好像我必须要去追寻姐姐,不成功死不足惜似的。“我知道她在哪。回家再告诉你。你饿不饿?”父亲把外套披在我身上,打了出租带我回家。路上父亲没透露一点关于姐姐的消息,我心里空落落的,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到了家他给我找了些吃的,说要坐下和我聊聊。“其实我也没有她的消息,但是我可以陪你一起找她。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不懂你姐姐,我感觉很多话她都只对你说。她都和你说过什么?或者带你做过什么?”“你真的要听我讲吗?其实有时候我会怕你,怕你不喜欢我听我说这些……”“真的。”他露出了一个难得的真诚的笑容。“姐姐会变成很多东西,你知道吗?就是那些难以置信的生物,或者我更愿意把她的那些状态命名为灵兽。我把我们之间的事都写在这本笔记里,我管它叫《眉寿书》。或许你看看就会有一些线索。其实……我不该这么冲动,至少应该和你们说一下。”“没事,我能看看这个本子吗?”父亲从我手里接过这本厚厚的《眉寿书》。他的表情写满不可思议,“以前没发现你这么能写,也许我也不太了解你。”“不不,你知道我不喜欢和人说话,但其实……我很想和你们分享,但你不会笑我幼稚吧……”把《眉寿书》递给父亲时,我欣喜于他想要了解我,可我的内心是忐忑且害羞的,所以编出来一句话:“我……我困了,想去睡觉……”我醒的时候,母亲和父亲都在我床边,满脸愁容。父亲说道:“你起来,我们来客厅谈。”等我落座以后,父亲把《眉寿书》扔给我,语气伤心中夹杂着轻微的怒气:“我和你妈妈终于知道你这些年魂不守舍的理由了。你识字早,机灵,很少让我们操心。你在学校里几乎不和人说话,老师看你天天上课写东西都拿你没辙。我们以为文学只是你的爱好的,只是没想到你就这么误入歧途了。”他又叹了一口气继续说:“你知不知道咱们家就从来没有‘姐姐’这个人。不,那个怪物。从八岁开始,你张嘴闭口就是‘姐姐’、‘姐姐’的,我们纠正你一遍你就忘。很多次我们以为你在逗我们,直到这件事持续了快十年我们才看出蹊跷。你在和你故事里的人物说话,你明白吗?女儿,从来没有东西和你并肩,从来就没有姐姐。你知道你自言自语,自己和一个写出来的人物对话的样子有多可怕吗?还有你一个人对着动物说话……今天你甚至离家出走要去找她。什么困世山、冽凉山,那都是你自己写下来骗你自己的!”“不可能……是你把她关起来的呀,是你给她建了一间密室啊。我带你去。”我站起身来,拽着他到我卧室来。 当我进到卧室的时候,我害怕地看向四周,怎么都是白墙?不可能的呀。“不,门就在哪儿啊……”我指着一面墙的某个位置难以置信地说道,“不,是你告诫我不要把她放出去的呀。不可能……这不可能……姐姐是假的……姐姐怎么可能是假的,姐姐那么美好的事物怎么可能是假的呢……”我转身看向惊魂未定的父亲,破口大骂道:“不对,是你把她带走了是不是?是你们把她抓走了是不是?你们不能把她带走,外面的人真的很吓人……只有姐姐我才能不孤独,只有姐姐我才能不孤独,你们懂不懂?你们懂不懂啊?”我拿起书桌上的书狠狠地砸向他,自己已经泣不成声,几句呐喊过后声音沙哑。父亲在害怕中越躲越远,最后我愤怒地把他从我屋子里赶出去,反锁了门。我一个面对姐姐密室大门原来在的位置,收住了眼泪,强迫自己用手抚摸这冰冷的墙。我一个静静地抚摸着,这才发现它是如此天衣无缝,仿佛从没存在过一个门,没有任何糊死的迹象。我惊愕地又哭起来,随后我开始用头狠狠撞向那墙,一边撞一边喃喃自语道:“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呢……一定有姐姐的……一定有门的……不对,一定有门的。”我一边撞一边绝望地想着。此时太阳化作巨大冰冷的枪口伸向冽凉山,屋内我猛烈的撞击和父亲的刺耳的敲门声,声声都是枪响。冽凉山在一枚现实的子弹之下,化为了一捧灰烬。那灰烬随风飘散的声音,就像我曾经模仿着一个死去的诗人对着世界问道:“尔有觌于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我听见《眉寿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成了耳畔循环的经文,看到地板渗出水来拼凑出姐姐的脸,看到她伸出双手想要从墙缝里爬出来,而那墙缝死死地卡住了她叫她动弹不得。我绕着这屋子的四角跑来跑去,想要去救她,可她像只难捕的蝴蝶,轮廓被我发现的时候就逃走。此刻我感到自己也被囚禁在一间没有出口的密室里,一口蒙灰的钟之中,我用身体狠狠地敲打着它的四壁,没有裂痕只有回声。很快我感到压抑的空气变成了涨起的洪水,我感到嗓子已没什么力气,而一口巨大的血痰封住了喉咙让我无法呼救。我的额头开始流血,沉重的红色花瓣打湿了我的眼眶……我疼得睁不开眼睛,身体筋疲力尽,脑海里只剩下要写在《眉寿书》的最后一句: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于是我使出最后一口气狠狠向墙撞去。就在我倒地的那一刻,我听见……我听见门开了。(全文完)作者简介:陈陈相因,年9月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现为复旦大学21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曾出版十六万字个人小说散文集《以梦为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年09月),小说见于《青春》《小说林》《石油文学》。(作者肖像摄影:张铭航) 陈也野仅仅完成我的一生。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idiexianga.com/mdxhy/9425.html
- 上一篇文章: 调料界的ldquo哈利波特rdqu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