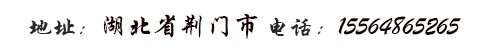他只当我是落魄乞儿把我养成好用的刀,竟不
|
帝崩三月。我于人群望萧景予,坐拥山河,接受百官跪拜。 正欲功成身退,他说:“阿肆,再帮我做一件事。” 阿肆。 是他给我的名字,我是他在街头捡的乞儿。衣衫褴褛,腹中时时在唱空城计。头一回见他,他说只要我听话,以后就不用挨饿,问我愿不愿。这种好事我当然愿意了。 我的名字,是排在三位同门的后面。他说,他不要无用的人,所以他们都死了。 我打架毫无章法,只知道咬人。萧景予找人教我如何用刀,如何用暗器,如何下毒,还教我歌舞,可惜,我永远学不会那些柔媚体态。 我第一个任务,是刺杀弹劾萧景予的孙大人。 孙大人说萧景予贵为三皇子,纵容属下私吞赈灾银,这又与我有何干系。他府上小妾需要丫鬟伺候,我便打晕了一个小丫头,借着送茶摸清他的卧室。 月黑风高夜,孙大人的房间最后一丝烛火熄灭,我在屋瓦上等到四下,只听见他旱雷般的呼噜声,腰上绑了绳子,便倒悬挂房梁。 说实话,我也没想好怎么杀他。 因为萧景予说,得做的滴水不漏。不能让一个弹劾他的人,第二天就直接暴毙,以此留下把柄,让他受老皇帝怀疑。 挺刁难人的,刚好绳子放完了。我站他床边,一直在想让这个孙大人如何完美死去。 第二天阳光暖暖,孙府说孙大人纵欲过度,死在新娶的小妾房里。 六个自称小妾的女人,说她们是被孙大人强娶豪夺的良家女。孙大人的名声直线下降,流言四起,各种为官不仁的冤假错案,使皇帝暴怒。 萧景予夸我办得好,我吃完一个鸡腿说。 我怕。 他说我看着一点也不怕的样子。 临走,他说,他不要无用的人。 我知道他在警告我不能怕,也不能心软,否则就像前面三位同门一样,尸骨无存。 此后的任务,越来越多。他总会在书房里,兴致勃勃地听我是如何下手,如何毁灭痕迹,以及如何颠倒黑白,将良臣化作奸臣败类。 老皇帝身体病重,萧景予到榻前尽孝。与此同时,我远赴雁州,将府州女儿来了一场狸猫换太子,萧景予说,要言府上下一个不留。 两鬓斑白的老人,对我和颜悦色。我先前学的那些冷硬心肠,有什么裂了。耳边回响,萧景予说他不要无用之人。 我大概算无用之人吧。 天干物燥,言府上下十五口人死于大火,火光冲天,附近百姓救了一晚上。天边翠微初晓,蓝色的烟轻轻袅袅飘浮着,一具具担架盖上白布,正好十五个,一个不少。 百姓说言老爷为官清廉,纷纷跪地哀嚎,我于人群后面,静默地看着。 萧景予当然不会信我,我还有一个搭档,她叫西尧。 不过是我负责动手,她负责给萧景予传递任务进度。看起来,她比我等级还要高。 她也在这里,乔装成衙役一个个验尸一遍,事后她说:“阿肆的心真的好狠,言老爷那么疼你,你怎么舍得不要这点温暖?” 我不在意的擦着手里的刀刃:“他只是疼他女儿罢了,我不是,多简单。” 我们回去时,关于弹劾萧景予的奏折越来越多,多到他脾气越来越暴躁。我也越来越忙。 老皇帝病逝三个月后,他说:“阿肆,再给我做一件事。从此你就自由了,再也不用血染双手。如何?” 条件真的诱人,我匆匆点头,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是要我嫁人。 嫁人应该做什么,做饭我不会,洗衣服我也没做过。他难得亲口告诉我:“只管看好你夫君罢了,他去哪里,见了什么人,与何人交好通通告诉朕。” 黄袍加身,他看起来意气风发,却忌惮一个九皇子,萧念安。 这名字真好听。 看起来我也像西尧一样,执行监视任务。 我摇身一变,成了王府义女,嫁给九皇子萧念安。 嫁妆嘛,就萧景予送的一支簪子。 其实嫁妆挺多,萧景予没什么不好,就是财大气粗。 簪子是我最好贴身带着的,他给的那些嫁妆,听说从王府进了九皇子府,走了一条街都没有走完。 新婚夜,我第一次见到萧念安。 他简单一身红衣,是个安静美男子,掀开盖头,冲我浅浅一笑,问我:“我在哪见过你呢,你叫什么?” 我脱口而出:“景洺。” 这景洺,是萧景予给我起的第二个名字。方便我卧底。 萧念安念了两遍,摇摇头。 “听起来像某种瓷器,生冷,换一个如何?” 我换了舒服坐姿,左腿压上右脚,盘在床铺上等他下文。看起来随意极了,一点没有大家闺秀应该有的样子。 “有诗云: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苏有万物复苏之意,叫苏海棠如何?或者苏胭脂,苏香雪什么的。” 烛火摇曳,他剑目,一双眼睛里尽是我的身影,我坐的这般随便,全身上下没有一点新娘子应该守的规矩。 其实,我想说我不喜欢海棠,但是,他前面说,苏有万物复苏之意。我又欣然接受这个新名字,我姓苏,唤海棠。 听起来还不赖。 萧念安,苏海棠。我心里默默来回咬这两个名字,念了五六遍,倒是惦记吃的起来,一想到海棠,就想吃海棠果。 小时候住的破庙,有颗海棠树,我没少为上面还未成熟的果子打架,把几个大孩子掀翻,就爬上树霸占那些还是青色的果子。 不管多涩多苦,都吞下腹中,只要这里没有果子了,还有谁来天天和我打架。 打架特别耗费力气,好不容易吃半截馒头,打一架下来,肚子又要咕咕乱叫。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才不要。 萧念安修长的手指,在我眼前晃了晃:“怎么,不喜欢吗?我再想想其他的,比如蓝田玉暖日生烟,苏蓝烟好像也不错,对吧?” 我算是发现,这两兄弟的共同点了。都特别喜欢给人起名字,一个没文化,一个有文化就很可怕,一晚上下来,我有百来个名字。 全是萧念安从古诗里给我取的,我们的新婚夜,我听他背了一晚上的诗,真的也是没谁了。 偏偏他取的名字,每一个我都喜欢,到最后都不知道选哪个名字好了,我懒得想,直接要了他给我起的第一个名字。 他说:“故里念长安,长安有海棠。你看,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多般配。” 这算是他和我说的,第一句情话吗? 果然有文化的就是浪漫。我嚼着那句长安有海棠,唇边勾起灿烂笑意。 有名,有姓的苏海棠。是念长安的海棠,海棠心意藏于心底,不与人说。 萧念安这个人,就是个爱书成痴的呆子。吃饭看书,喝茶看书,听戏时看戏文,还教戏子哪里需要深情唱什么,故人已归去,徒留子孙泪。 如何提笔给萧景予汇报进度,我倒是犯难了,这皇帝没教我啊。 我玩了一下午的墨水,萧念安进书房换书看时,看见我脸蛋上,衣服上全是墨水,像只黑白色的大花猫趴他桌子上,笑到腹痛。 他无奈捏起一角衣袍袖子,仔细擦了一下我的脸,眼里全是我的倒影,里面的我颇有些狼狈,就差往脑门刻下花痴二字。 九皇子萧念安的盛名,人人皆知,我只知道他貌美无双。这还是西尧告诉我的,她只说过这一句。 “在做些什么,你看看你,就剩下那双眼睛好看了。” “我眼睛好看?” “自然,清澈如水,当然好看。” 怎么好看呢,我怎么值得他说我的眼睛看起来清澈如水?不过,有人夸我,我就很开心。 “萧念安。” “嗯?” 我又唤了他一遍。 他耐心回应,眼里笑意满满,我大概要醉了,大概要溺在他的目光里。萧景予那句无用之人,又在我耳畔炸响。 “萧念安,教我写字怎么样?” “好。” 他教我写字,写的是他的名字。我的字写的又大又丑,一张纸一个字浪费着,后面他亲手拿出小时候练字的沙盘,让我在上面写。 我有些委屈巴巴:“太小了吧。” 他比较了我们两者之间的差距,终于知道沙盘尺寸有些小了,不适合我这个大孩子玩。便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木板框,上面铺满细沙。 “请赐墨宝吧,夫人。” 我拿笔的动作微微停顿,萧念安,你知道后,会生气吗? 他的名字我写了几百遍,只有一个萧字看起来不像样。 “这一笔不要那么翘,你要翘上天,还是要逃到哪里去?” 我微微吐舌:“习惯了嘛。” 话音刚落,我便不再出声,我开始学着撒娇了。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做人家妻子,需要和夫君撒娇吗? 西尧半夜到我窗前,差点被我的话笑岔气,幸好萧念安中了迷迭香睡得香甜。 西尧说,我只管与萧念安卿卿我我,萧景予快收网了。 收什么网? 萧景予一个皇帝要对付一个九皇子,还需要收网吗? 萧景予的生日,我和萧念安一同给他祝贺。宴会上,百官欢聚,香袖艳舞,热闹极了。 萧景予怀里抱着一个貌美的女人,我和萧念安坐他左下角,能清晰看到,她眼角下的泪痣。她对我调皮的眨眨眼睛,天真烂漫。 萧景予变得有些荒唐,他一会换下刚才的女人,转眼又抱了另外一个身材有些肉感的小女人,吃着她喂的葡萄,一脸痴迷地回吻她的唇。 辣眼睛,我忙碌的剥着橘子,一一喂进萧念安嘴里。最后一片往往进我嘴巴,我什么东西都喜欢吃最后一口。 男人之间的谈话,听得我云里雾里,两个兄弟你来我往间,天地都变了颜色。 萧念安慢条斯理地拨开橘子上的细丝,塞进我嘴里,唇放我耳旁,暧昧的呼吸撒到我耳垂上:“夫人应该这样喂为夫。” 我被他弄得耳朵发痒,脸不自觉红了,在萧景予位置看来,他的阿肆将他九弟迷到神魂颠倒。不顾皇威,在众人面前与爱妻耳鬓厮磨。 重阳节那晚,萧景予的妃子邀我入宫。 萧念安送我到宫门外,笑如冬日暖阳:“晚些接你。” 我嗅着他衣服上的松柏薰香,痴痴地笑着点头,被美色俘获的我,恋恋不舍的离开马车。 他在马车上,我在马车下站着,他的一双手被我握住。 我力气有些大,他不得不附身靠近我一些,我吧唧一口亲他脸颊,红了老脸,飞快跑进宫门。 这算我们成婚后,第一个吻。 萧念安笑得轻轻浅浅,放下帘子就离开了。马车在青石砖的小路留下两道痕迹,天边的晚霞依恋的靠近连绵山脉。 到了宫里,我没有见到萧景予到妃子,只看见萧景予一个人。 宫门紧闭,我被他幽禁起来。 他说萧念安举兵谋反,我当然不信,他就是个喜欢吟诗作对,在新婚夜背些美诗,教戏子何处翘指的闲人。 萧念安起兵,从萧景予嘴里听起来像是个玩笑。而且与我何干,把我关在这里,是我的任务结束了吗。 萧景予先前答应我的天高海阔呢? 他的轮廓愈发凌厉,像随时扑上来撕咬的猎犬。我知道把一个皇帝比喻成猎犬不妥,但是我也只知道,一头饿极的猎犬什么都会咬。 “听说你在学写字,萧念安有没有教你什么伉俪情深这些?” 我动了一下脖子,差点习惯性摇头,而萧景予讨厌摇头,我只能老老实实回他:“自然没有,只是写他名字。” 他忽然咧嘴一笑:“这就够了嘛。” 他叫来两个小太监,用竹夹板套上我十根手指:“我想帮你赌一赌,你在他心里的位置。” 两个小太监各自往不同的方向用力,十指连心,豆大的汗珠从我额头滚下来,没有萧景予的命令,他们只管狠命的拉着。 我撑不住喊出声,萧景予拍手笑道:“就是这样,别停,别让她太舒服。” 他凑到我面前:“赌一个男人会为了一个女人,会做些什么。你猜他对你有没有爱?或者我们赌一赌,他到底救不救你?” 我疼得说不出话,挣扎着想把耳边嗡嗡作响的苍蝇赶走,整个人俯跪到地上,企图以体重压制那两个小太监,让自己能得到一丝丝薄弱的喘息。 萧景予的眼里,我是那么狼狈,如同案板上的鱼,任他宰割。他当然可以给我一个痛快,可他偏偏要拿我,去赌萧念安对我的在意。 萧念安,他怎么会在意我呢? 我们相处不久,不过起个名字,听几回戏,教了几个字,怎么就值得在他心里得到一点位置。 萧景予扯下一张白布,铺在我面前:“写,用你的血,写他的名字,写他萧念安的名字,我就让他们放了你。” 他将白布再次推过来:“我们就赌一赌,他看到这个,到底救你,还是不救。阿肆,你最好了,就这最后一件事了好不好?” 他最后一句话,像讨糖吃的孩子一样,贵为皇帝的萧景予竟然和一个杀//人机器讨糖吃,听起来真的匪夷所思,对吧。 我只想着这十根手指,实在太疼了。脑子里昏昏沉沉,半点力气使不出来,有什么热热的顺我脸颊流下,滴滴砸落到冷冰冰的地板上。 “阿肆,别哭,只要你按朕说的做,天高海阔,朕说到做到。现在只有你能帮我,扳倒他,你就自由了。” 一个萧念安有什么值得他忌惮,一个皇帝要打击自己的骨肉同胞,竟然想出这么个损招。他凭什么以为,萧念安会在意我。 他撤了竹夹,扯过我的手准备自己写,我挣扎着将手拿了出来,颤抖着声音:“陛下,让我自己写吧。” 他高兴像个孩子一样:“阿肆,快写,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一个萧念安会对这带血的信做什么反应。” “陛下为何会肯定他在意我?” 他像触到逆鳞一般:“你们在宴会上那么亲密,连朕都不放在眼里,他怎么不在意你!” 我惨兮兮地用手肘撑着身体,笑他无知又天真:“陛下就没有看戏过吗?” “戏?阿肆,你们骗我吗?” 我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就当我骗他,即使是水与鱼的缘分,我也甘之如饴。” “不要!阿肆,你不是鱼,他也不是水,你们加上一把火就是鱼汤有什么好。” 萧景予疯了一般摇晃我肩膀,手肘磨地,十指肿痛,除了想到狼狈二字,我找不到别的词汇,形容我现在的处境。 贵为天子的萧景予,反复把那白布拿到我眼前,口中不断重复,要我写萧念安的名字。 我就是再蠢笨,也看出他想用我牵制萧念安。 可是萧景予,你压错宝了,谁会爱上一枚棋子? 他换下竹夹,上了一个新鲜玩意:“这个是朕命人精心打造的鱼线,是铁线打出来的,把你这些血肉割破,吊到城外,他还敢和我对账吗?” 萧景予踢开白布:“不写也可以,朕要你自己去看,萧念安到底在不在意你。朕得不到的,他如何好过?” 我艰难的撑起身子:“陛下已经这江山的主人,到底在怕些什么。一个萧念安值得你那么忌惮吗?” 萧景予疯了一般摔着袖子:“不够,他在朕面前晃悠一天,朕就不安心。放虎归山,总有卷土重来一日。索性,毁了他所有在意的一切。” 他扯着拖着,把我带到城上。城下,萧念安骑着枣红烈马,一身盔甲,他的身后乌泱泱站着几十万大军,甚至远处还有许多墨点往这里移动。 不止几十万大军,一些高官愤恨指控萧景予的残暴。我好像看见言老爷也在百官其中,他想冲上来说些什么,被人拦下。 他的头发已经是苍白色,红着一双眼眶看着我,看得我鼻子发酸。 幸好萧景予不认识他。 城下的孙大人破口大骂:“老夫一生为亡妻守灵,一身清誉竟然被你这肖小颠倒黑白。你容翼党私吞灾银,浮尸千万已饿死,你不配为君!” 言老爷颤颤巍巍地,指控萧景予:“毒害先皇,篡改旨意,为君残暴,荒淫无度。” 萧景予死死用鱼线勒住我脖子:“萧念安!你现在退还来得及!否则朕杀了她。” 白衣将军脸上波澜不惊。 “萧景予你看,你赌错了,他怎么会在意我呢。” 萧景予不敢相信我敢叫他名字,手上松了几分力道,似乎要我继续说下去。 我得到一丝喘息,正了正心神,眼睛一直看城下的萧念安:“萧景予。我从来不是乞儿,我也有父兄,我也有姊妹,我是家里最小最贪玩的。” 萧景予手上力道加了一分:“这与我有何关系!” “当然有关系,十三年前,我父兄困于关外,你扣留粮草,通敌叛国,将行军图送给蛮夷,使我父兄尸骨无存,三十万大军惨死西北。” 我被他勒紧,快喘不过气,只能用痛到麻木的手,去和他争抢那根鱼线,握住它的瞬间,鲜血淋漓,痛入骨髓。 “我们家上下一百五十五人,算上旁支二百一十人,通通被你一把火烧死,你是不是想说,我怎么还活着?” “我贪玩掉到旱井,整个晚上听见外面的惨叫声,你知道让一个七岁孩子有多害怕吗?” 萧景予疯狂的笑着:“所以你,一开始就算计好要背叛我?” “怎么叫背叛,这是你欠我的,你还能记起我父兄的名字吗?” 萧景予哈哈大笑,眼角笑出眼泪:“怎么会记得呢,死朕手上的人,怎么配拥有姓名!” 我用力绞着鱼线,任由它划破脖子终于把它,从萧景予手里抢了过来:“我姓傅,我父兄镇守祁连关二十年,怎么样,能不能想起一丝一毫?” 萧景予退了几步,后知后觉:“你是亲王傅楼的女儿?” 我笑了笑,并没有反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你看看你,坐上这江山,自顾自己舒服,不管百姓死活,他们都不愿意载你了。” 萧景予眼里有些茫然:“阿肆。” 萧念安民心所向,眼眸微暗看我们在城上拉锯。我对他展颜一笑。 “萧景予,还有一件事你不知道,我认识萧念安比认识你还要早。” 焦烟漫天的夜晚,他逆着火光把我从井里救出来,他说,梨落,对不起,我来晚了。 他为何要何我道歉,真正的元凶明明是萧景予,我虽然年幼贪玩,该知道的,父兄出征时,早已经把一切告诉我。 烟火熏得我眼睛生疼,我攥着少年萧念安的衣服,一字一句说我要报仇。少年答应帮我。 彼时少年只是比我大三岁,个子高挑,将我护在怀里,冲出火海。我看见他一片衣角翻飞,我看见姊妹身上衣裙被血水染红,死不瞑目。 每每梦魇,我如同失去氧气的鱼儿在梦里苦苦挣扎,萧念安总会守我到天亮。 梦魇连续折磨我三天,萧念安说我要忘记这些,既然想要报仇,必须把所有弱点藏起来。 城里一处破庙多了一个乞儿,这乞儿打架凶狠,只管用两颗利牙咬人脖子,凶残可怕,更可怕的是竟然还是一个小小的野丫头。 我不知道我过了多久乞儿日子,三个月或者是五个月,萧念安安排每天,给我半截馒头的姨娘告诉我,萧景予的人盯上我了。 我刚结束和其他乞丐抢一棵海棠树的斗争,鼻青脸肿,头发混着泥巴和树叶,要多不堪就有多不堪。 肿着一边已经成紫色的眼睛,在树下刻着自己的记号,因为名声在外,我用石头刻的一颗尖牙还没刻完整,他就来了。 衣冠华服的萧景予笑眯了眼:“小东西,你在做什么?” “刻记号,这样他们不敢再抢我的果子了。我咬人很厉害的。” 说完,我亮出自己两颗尖尖的虎牙,笑得不知所谓。 他一把夺了我手上的石头,直接扔了:“只要你跟我走,听我的话,你再也不用和别人抢一棵树,挨一顿饿,怎么样?” 舌尖划过利齿,我瞥了一眼他的脖子,仇人近在眼前。萧念安说过,人的脖子有根命脉,一旦遇上疯狗,会死的很惨。 腹中咕噜作响,让萧景予笑了起来,他牵着我离开破庙。 我从车窗望那棵海棠,刚来时它的枝丫光还是秃秃的,从花开到缀满青果,原来小半年已经过去了。 我不需要和人争夺食物,只需要跟着萧景予给我安排的各种师父,学习如何去暗杀目标。 要是错了一步,让萧景予知道,他会亲自用鞭子打我。 学跳舞那阵子,打得最厉害。 我死活学不会下腰,跳错了一步,萧景予的鞭子就噼里啪啦落我身上。 七月,他准备让我在中秋夜潜进九皇子府献舞,可我老是卡在第七步。 第七步,要一边笑,一边绕着腰,舞娘还说要媚眼如丝,去勾主位人的魂魄。我又不是黑白无常,干嘛去勾萧念安的魂魄。 于是,院子里三天两头都是鞭子声,萧景予打完了还要亲自上药,比杀了我还难受。 他打人也讲技巧,让我跪在院子里。舞着手里的银蛇鞭子,使劲往我背上招呼。大概皮厚,每次他打我,我就死死咬住下唇,双拳紧握,不许自己发出一点声音。 萧景予打累了,又拿上最好的药,不许我留一点疤痕。上药明明可以让西尧帮我,偏偏他要亲自来,好多次,我差点憋不住想直接杀了他。 攥着的拳头因为萧念安说过的一句,杀//人何不诛心,缓缓松开。 萧景予教我杀的是人,萧念安教我如何毁心。 中秋夜我跳得不好,萧景予却高兴坏了。他说萧念安看上我了,我暗自笑他陷入环中环,还不自知。仗着自己是他手下有用的人,对萧念安大贬特贬。 萧景予因为心情极好,躺我腿上。马车摇晃,我的手抱着他的脑袋。他听着我将萧念安贬入尘埃,笑得越发得意。 听他笑声,我差点忍不住五指成爪,就将这杀我父兄,害我姊妹的凶手,即刻扭他脖子,送他去阴司与我至亲赔罪。 我一忍再忍,萧景予往老皇帝面前尽孝,每日往皇帝熏香下毒。而我扮上言府小姐时,言父说我像极了我母亲。 言父是伺候我母亲的老人,对我万般关怀,可怜我被萧景予害的三岁丧母,七岁丧父。世家言官帮我暗网张网,将萧景予各种罪证集齐。 我与萧念安的新婚夜,我将萧景予的种种把柄,交到萧念安手里。 红烛照着我的脸,我问他:“这些够诛心了?” 萧念安将我抱在怀里:“梨落,已经足够了,接下来交给我,你什么都不用管。” 我把玩他修长的手指:“我要亲手杀了他,你会不会念你们兄弟一场,恨我?” “皇家无情。等一切尘埃落定,我带你去西北,你父兄还有傅家所有人,我都葬在一处有山有水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男耕女织如何?” 我勾起他垂于胸前的墨发,玩的不亦乐乎:“这江山你不要吗?” “得海棠梨落,已心安。” 我和萧念安止乎与情,守与礼,相敬如宾。重阳节那天的吻,是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吻。 萧念安你不懂,猎犬一旦发疯,不死不休。 萧景予猩红着眼睛质问:“所以你,是他一早安排的棋子,只为了把朕拉下皇位?” “对呀,所以,下棋的人会在意他的棋子吗,棋子走哪里还不是他说了算。陛下做对了一件事,就是让我这个棋子嫁了萧念安一回。” 萧景予慌了,掐着我脖子:“怎么不在意!阿肆,朕错了,朕不该让你嫁他。跟朕走,欠你的命,我尽数还你好不好。” 我笑:“陛下,我不是阿肆。” 萧景予在我耳边吼:“你就是!生是我的,死也是我的。萧念安,眼睛是骗不了人的,朕知道你在意她,朕得不到江山,美人也不会给你!” 萧景予随身匕首刺进我胸口,城上暗处藏的羽林军,万箭指向萧念安,萧景予笑得已然疯魔。 我吃痛看了眼伤口,城下的萧念安气急攻心,咬牙切齿地喊萧景予的名字。 “萧念安。你拿什么和朕打?这天下,通通都在朕脚下。除非你自刎阵前,否则我这些羽林军万箭齐发把你穿成刺猬!” 萧景予数三个数,胜券在握。 我亲眼看着萧念安拔出佩剑,心下一横,疾步捆了萧景予的脖子,背靠城墙。 我威胁那些羽林军:“我父兄守边疆杀敌盛名人人皆知,他萧景予能为一己之私,杀我父兄。你们不怕有日与我父兄一样含恨九泉,就尽管放箭。” 萧景予看所有羽林军放下弓箭,气急败坏:“阿肆!” 狼烟四起,我最后看了眼湛蓝的天:“萧景予,我从来不叫阿肆。” 暴君下台,五皇子萧远仁登基。 茶余饭后,人们说起那日,忍不住惋惜我,为了让萧念安再无牵挂,竟然同暴君一同坠楼。青春年华,可惜可惜。 大仇得报,我该了无牵挂。 为何地府黑白无常,不来为我引路。 我变成游魂,徘徊城上,亲眼看黑白无常勾了萧景予的魂,他被万鬼撕咬着。其中是否有我父兄,我也不知道。 黑白无常离开之际,我追了上去问他们干嘛不带我走。 他们说我生魂未灭,勾个屁。 竟然还有这种说法,我便只能飘飘荡荡,新帝信佛,经常请高僧吟唱佛经。 每次我都在高僧面前张牙舞爪,看得见我吗,看得见我吗? 显然,抛着银子喝酒的高僧看不见我。我闷闷不乐坐城墙上,生前流浪就算了,原来死后也是居无定所。实在可恶。 是哪一日呢,我看见一个光头的人,长得特别像萧念安。 我便跟他进了新帝行宫,光头版萧念安和新帝下棋。偶尔吐几句佛法。 仗着没人看见我,我坐他们旁边破口大骂:“你这秃驴,饭吃了几斤,就在这里装深沉,还长了张我夫君的脸,木鱼敲够了吗,功德满了吗?” 秃驴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弯的,和新帝下棋到半夜三更,才提灯离开。 我跟了他一路,无非说他可能和萧念安一母同胞,可能是老皇帝流落民间的皇子。说他一点审美都没有,萧念安怎么舍得剃那么漂亮的头发,当一个丑拒的秃驴。 他进了佛堂跪下,我缩太缩脑的钻进去,佛祖在笑,他也在笑。 我安心的学着他盘腿坐下,他敲木鱼,我手里又没有什么能敲的,看他光头实在喜爱,便给了好几个糖炒板栗给他。 唉,总是打空气也是无趣。 “下一晚上棋就应该睡觉,现在还敲什么木鱼!” “因为功德还没满。” 吓死鬼了,原来他能看见我。一定是佛祖庇佑,看我太寂寞,让他陪我说说话。 “我是老皇帝一夜风流?还有一母同胞?梨落,还是那么调皮。” 萧念安说,那天我用力过猛,推萧景予一同坠楼,自己的魂魄脱离本体,只有至亲日夜祈福,才能起死回生。 “这就是你当和尚的理由?” 他说:“无海棠,便无念安。”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 父亲最爱这一句,我出生时树上梨果香甜。我长到六岁,整天仗自己人小鬼大跟在萧念安身后,父亲教他们剑术,我在一旁炫耀自己咸鱼一条。 我被父亲罚在树下蹲马步,萧念安在一旁念诗,夫子嘴里无聊的诗句,从他嘴里说出来真的好听极了。 “要是我一辈子都是游魂,你怎么办?” “那就敲一辈子木鱼,渡你。但我信佛祖,会让念安有海棠。” 唉,佛祖果然听他的,不然我怎么会在这酒坊当老板娘呢。 全文完 更多古风好文点击下方专栏即可订阅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idiexianga.com/mdxzp/11588.html
- 上一篇文章: 不要再骗了,大牌平替就是个圈套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