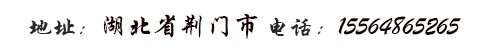小区改造,菜农们集体失业了
|
北京白癜风治疗技术 https://jbk.39.net/yiyuanfengcai/tsyl_bjzkbdfyy/ 卢老师的菜园的春天,夏天的时候茂盛得像小树林 的贾老师轻轻敲门,分享她家菜地里新收的红薯和芋头。红薯个头小小的,挺可爱,据说要到八月十五之后红薯的糖化才充分,口感更好。 贾老师说,一点点,聊表心意,拿不出手。 其实,是再也没有啦。 贴在小区里的老旧小区改造宣传广告(图by作者) 老旧小区改造,我们东区榜上有名。业主群里争争吵吵,热热闹闹,保留热水器、防盗网、雨阳棚……,主张物权法所赋予的权利……,各路神仙,莫衷一是。 改造工程的项目包括整修外墙,楼顶防渗漏,小区绿化等等。 物业在群里发通知:各门栋屋顶上的种植箱等各种物品,必须按时清理,以便施工。 然后,某一天,小区里,搭起了脚手架,围上了绿色的防尘安全网,钢管碰撞的脆响,铁锤砸废热水器的沉重,俨然一生机勃勃的大工地。 于是,生机勃勃的楼顶菜园,在几天之内消失。种菜的邻居们提前挖了红薯、芋头,拔掉还在生长和结实的茄子豆角辣椒,拔掉绿油油的韭菜、香葱、生菜苗儿…… 几天前还生机盎然绿油油的菜园,变成了废墟,与钢筋水泥的背景很配(图by作者) 在我们的楼顶菜园中,卢老师的菜园最是琳琅满目。除了各种应季的蔬菜,他还种花种果树。他有一棵长了很多年的柚子树,一对白头翁在树枝间做了漂亮光滑的窝。他还有一棵很大的栀子花树,每到夏天,缀满洁白的花朵,香气扑鼻。这些都因为体积太大无法搬运到阳台而无奈放弃。 为此,卢老师特地用历年所拍的照片做了一个美篇,写道:这曾是一个位于七楼楼顶,由一个个泡沫箱构筑的空中菜园。在菜园周边还有盆栽的绿梅、腊梅、无花果、栀子花,甚至还有一棵从种子培育起来的,已有一人多高的柚子树。树上有白头翁筑的巢。可惜,旧城改造后,菜不让种了,花也不让栽了,关于它的美好记忆只能来美篇寻找了。 柚子树上的白头翁雏鸟 贾老师为在外地的邻居代管的大棵的月季花、翠竹和花椒树,也被迫放弃。她和另一单元的邻居家的黄豆长势旺盛,正在灌浆,舍不得拔掉,据说她们准备将手推车派上用场,需要的时候将种植箱搬上车,采取游击战术,直至黄豆荚稍微饱满起来。 长豆角 峨眉豆开花 我开玩笑说,作为菜农,我们集体失业了。 失去菜地的邻居,仿佛一夜之间没了捞摸。这么多年来,只要早上去楼顶,定然会看见贾老师卢老师和其他邻居们在朝阳下认真浇水施肥整理菜园子的熟悉的画面,突然就不见了。从前傍晚在楼顶上边劳作边交流的有温度的传统农耕生活的场景,也消失了。安静而空荡的楼顶,让人好不习惯。 没有了那一片片绿油油、高高低低的种植箱,这楼顶,真的荒凉破旧啊。 种菜这些年,已经习惯了看楼顶四季不同的开花与结果,生长与枯萎,习惯了邻居们在楼顶上交换信息,交换种苗,关心天气,分享收获的喜悦……如果要评选最佳邻里关系,那非我们单元莫属。连住在四楼的年近九旬的张老师,天气好的时候,也会手里拿着健身球,上来瞅瞅看看,并开心地发表意见:你们的菜种得不错呀。 邻居们种菜的风格各有不同。或许是得益于当年的知青生活经验,卢老师是拥有绿手指的菜农,种植热情高,种植技术好,在有限的空间里发挥出了无尽的才华。除了品种更加丰富之外,他还对环境的整洁有极大的责任心,简言之,就是见不得谁家种植箱里出现野草和枯枝败叶。常常见他拿着扫帚到处打扫卫生,夏天的夜晚打着手电筒在各家的菜地里捉蜗牛。 为了防止小鸟啄光嫩嫩的小白菜,卢老师支起了好看的网子,有点像露营地 除了他和夫人在国外的时间之外,他家的菜园子总是整齐有序,生意盎然。而且他还是一个文艺型菜农,喜欢用相机记录他的菜园和劳动成果,分门别类地发到QQ相册中。从他的QQ相册得知,热爱种植的卢教授,走到哪里就把菜种到哪里,而且都是收获丰硕。 贾老师种的菜品种也很丰富,我发现她和张老师最喜欢种的是生菜,买菜籽,育苗,移栽,特别有耐心。细如发丝的生菜一箱一箱地长大,让我也跟着沾光。 我楼下的何老师是个大忙人,喜欢批量种植某些不特别费水的东西,比如生菜,小南瓜或者红薯。收获之后,将红薯挂着我家大门上,分享劳动成果。 而二单元的汪老师喜欢种小番茄,一大片的番茄树挂满一串串葡萄一样的小番茄,慢慢长大变红,特别诱人。 在楼顶散步的时候,在各家的菜园里穿行,看着日新月异的蔬菜,拍拍照,比较一下,心中很愉悦。 在所有种菜的人里,我就是那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佛系菜农。喜欢看黄瓜从柔弱的小苗儿逐渐长出几片叶子,抽条儿,爬上搭好的架子,开出明亮的小黄花,结出比指头还小的黄瓜宝宝,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凹出随心所欲的造型;也喜欢番茄从鱼卵大小到红艳艳的苹果般的番茄的过程。但最开心的,还是种花以及香料如薄荷罗勒迷迭香花椒香蜂草等。晴朗的春日,在温暖的太阳下,看海棠花在和熙的春风里摇曳生姿,月季花明艳芳香,便觉春光无限,人间美好。 春天的月季与海棠(图by作者) 夏天的黄瓜(图by作者) 在所有的菜农中间,我自然是最不勤劳的那一个,但也因此成为了受益最多的人。 比如,有时候早上还在睡懒觉,会收到贾老师发来的信息:刘老师起来了吗?我家的XX菜给你分享一点,我挂在你家门口了。有时候上楼去看看,她便塞给我一大把她家的生菜、秋葵、芥菜…… 而卢老师的口头禅是:想要么斯就直接克摘,不需要跟我说。他家的韭菜、栀子花、小番茄、黄瓜等等,这些年来没少享受。 卢教授是个文艺型菜农,拍的照片很美。这是他家的绿萼梅 记得有一年初夏,张老师问我要不要栽黄瓜,因为他和贾老师刚好弄到一些。我还没有考虑好到底种不种,就客气地回答等我有空把“地”准备好再说。过几天上楼,发现种植箱里,几株黄瓜秧子已经绿油油地长起来了。张老师和贾老师不仅帮着栽上,还每天负责早晚浇水。冬天,他们两位老先生还给我栽过芥菜、生菜、香芹等等。 下雨时,我放在屋檐下的储水桶里总是满的,那是热心的贾老师从她的大水缸拎来加上的。 架上累累悬瓜果 楼顶上这些美丽的菜园没有了,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毕竟物业对公共空间的管理是必要的。我们种菜,也难免让个别人不理解,甚至在业主群里批评。所以,我们都很注意不要影响别人,比如,贾老师和卢老师总是主动打扫地面,不给保洁师傅增加麻烦。 只是,一旦真要放弃这些投入了人力心力感情甚至财力,侍弄得越来越肥沃的菜园,心中的不舍,惋惜是真的。因为,我们从种菜中得到的乐趣,所体验的收获的快乐,是旁人难以理解的。 去年,隔壁单元的汪老师给了一塑料兜子她家种的小番茄,同学尝了后说:这才是真番茄,有番茄味儿。 可不是吗!种了菜之后,才又体会到自然生长自然成熟的食物的味道。在大棚菜、流水线的今天,我们餐桌日益丰富,年轻的人们甚至不知道真正的番茄黄瓜是什么味道。记得第一年吃到自己种的番茄之后,我有好几个月不能吃超市买来的番茄,那味道,感觉吃的是泡沫和塑料,味同嚼蜡,吃了想吐。自那之后,我每年都种恩施土豆、黄瓜和番茄,其他的菜随缘。 种菜的初衷因人而异。也许是为了吃到绿色健康的蔬菜,也许是对园艺对种菜的情有独钟,抑或是为了打发退休后的时间……。 吃自己种的菜,有一种安心。种菜让我们多少找回了记忆中食物应有的味道,也找回了与土地的某种联系。八零后的贾老师每天以种菜为锻炼,面色红润,眼睛明亮,声音清亮,精神特别好。 种菜也让我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道酬勤,依然是真理。 失去或者改变生活中的某一部分,也会改变与外界相处的一种态度,看待事物的一个角度。在开始种菜之前,我和邻居们的关系,大概是典型的现代楼房里的模式,见面点头打个招呼说声某老师好。但因为种菜,便有了更多的互动,也因此感受到更多的友善与热情。慧姑娘曾说她妈妈把菜地种成了社交平台,看来天底下的菜农,大抵如此。 像小树一样高的茄子 “别了,我的空中菜园;别了,我的都市农夫生涯” 卢老师在他美篇的结尾如此感叹。 在小说《飘》中,被白瑞德抛弃后,勇敢的郝思嘉准备回到她的陶乐庄园思考人生,底气是她父亲的话:“世界上唯有土地与明天同在。” 我们都早已被斩断了同土地的联系,所以,在钢筋水泥的缝隙里种菜,大概就是我们这些习惯了和土地打交道的人,最后的倔强和希冀吧。 在我们空空荡荡的楼顶不远处,那个无比巨大的商业体正在封顶;我们周围,越来越密集的高楼,阻断我们看洪山宝塔、看珞珈山的视线……我们的明天,与钢筋水泥的丛林同在。 (图除署名外,均为卢老师提供) 无限分叉的光与色 凌晨的雨,落在故乡的秧田里 文/海潮音 被滴答雨声敲醒时 窗帘和空调制造的幽暗与微凉 有一瞬间以为是在初夏的故乡 泥泞湿滑的田间小路 被雨水没过顶的秧田 长腿鹭鸶在低头寻找小鱼儿 塘边伸手可及又遥不可及的 荷花和逐渐饱满的莲蓬 顺着那条湿滑的小路 我早已远离所不喜的故乡 而故乡的秧田 也和当年的那些鹭鸶 插秧的父辈一起 住到记忆的天国里 躺在床上 听着凌晨嘈杂的雨 在紧闭的窗帘之后 生着都市人的怀乡病 或者乡下人的都市病 住不接地气的楼房 却时常想起故乡的模样 在楼顶种些不接地气的蔬菜 便仿佛有了连接故乡和父亲的媒介 醒着的闹钟 如节奏单一的雨点 固执地敲打着 失眠的疲惫 今晨的雨呵 请飘过天国里 故乡的小荷塘 飘过那条 再也走不回去 父亲走过的田间路 相关阅读楼顶种菜欢乐多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midiexianga.com/mdxjz/9933.html
- 上一篇文章: 发福厨房里栽上这10种植物,做菜水平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